从陈仓区的社区治理望出去,是千千万万个中小县城正在行进中的变革……
匆匆十年,陈仓主城区常住人口增长了8万。
在这8万人当中,除去因就业而新迁入的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周边乡镇的陪读家长。这些居民与区上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原城中村居民等汇聚,共同生活于这片1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单位家属院、“双鸥”“酒精厂”等老厂区,以及镶嵌其中的商业住宅楼,一群一群亮起点点灯火,照拂着静静的渭河和繁忙的铁道。
但在这祥和背后,社区治理正面临着挑战:人口结构的变化倒逼社会治理模式更新,如何才能冲破老旧小区改造难、单位型社区转型慢、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缺乏决策性参与等重重障碍?
陈仓区的做法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使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居民有效互动,朝着平安、便利、美丽、幸福的目标共同编织社区“多元共治”的网络。

给老旧小区“号脉”
在见到王德武之前,刘鹏已经散出去了200多份资料。
一年前,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辞去国企工作,应聘到全国连锁的H物业公司。彼时,企业需要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职工去拓展市场,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个人在开创事业和照顾家庭之间寻求平衡,两者一拍即合——刘鹏被派回自己的老家宝鸡担任区域经理。
“我们公司从2018年开始做老旧小区,现在物业服务已经涉及全国27个省市、65个城市,服务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这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中是很少见的。”刘鹏很坦率,“谁都知道老旧小区治理是片‘洼地’。”
这话正戳中陈仓区虢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德武的心事。
陈仓古称西虢,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而虢镇街道所管辖的区域从古至今都是“主城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供电局、信用社、农业局等陈仓区大大小小的单位家属院在此拔地而起。
随着社会变迁,国企改制,家属院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大量的老旧小区散落于虢镇街道的大街小巷,与毗邻的商业楼盘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现在家属院里住的很多是租户,给娃陪读的、进城打工的,城市低收入人群集聚。还有就是一些本单位离退休职工,虽然衣食不缺,但没有儿女在身边他们也就成了空巢老人。”王德武说,虢镇街道的管辖范围内共有87个老旧小区,其中没有物业管理的占到59个。
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安全隐患众多、环境卫生堪忧,这些小区成为王德武的一块“心病”——试过业委会自治,社区也尝试过成立物业公司,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物业管理应该市场化,而非政府兜底。”去浙江学习过先进地区的治理经验之后,王德武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治理好老旧小区,必须引进专业的物业公司。但几十户的小家属院单独请个物业公司费用上又不划算,怎么办?
刘鹏建议,把59个小区整体打包统一管理,这样双方的成本就都降下来了。而且考虑到这些老旧小区没有收费基础,他承诺前三个月可以先不收取物业费。
2022年5月,带着“先服务后收费”的理念和一套成熟的老旧小区管理方案,刘鹏代表H物业公司顺利与虢镇街道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刘鹏的物业服务是从安装一盏楼道灯开始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鸡人,参与到这场老旧小区治理的行动中,刘鹏有很强的代入感:这些楼房是他熟悉的家园,居民就像是他的亲戚四邻,带着感情做服务,他能一下子抓住管理的“痛点”。
“不要小看一盏楼道灯,它的意义不仅限于防止老人小孩上下楼梯时摔跤,更是一种‘家’文化的表达。我们希望,居民不管遇到啥事都能首先想到物业。”刘鹏说。
2022年盛夏时节,虢镇街道东街社区东关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散发出阵阵恶臭,污水顺着一楼东户单元门的缝隙溢出,一直流到楼梯间。可不凑巧的是,业主到西安照看孙子去了,因为疫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这事急坏了楼栋长冯庆民。这位72岁的退休老教师是陈仓区板羽球协会的会长,平常刘鹏在小区里遇见,他总是谈笑风生,“看我手里拿个板板(球拍),老头老太太们就都撵着来了”,很少见他这么火急火燎地。
虢镇街道的每栋居民楼都有楼栋长,大多是由冯庆民这样的人担任,为人热情、有威望、组织能力强,他们是城市社区网格管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出于对冯庆民这位老邻居的极度信任,一楼东户业主很快从西安寄回了钥匙。冯庆民第一时间,找到刘鹏帮忙。也正因为打了这么回交道,“冯老师”成了“刘经理”铁杆的支持者。
“我们进门一看,厨房水管堵啦,热天味道就闻不成么,物业的两个工程师傅硬是没弹嫌一句。修好了我喊他们上楼到我家洗个澡,也是小伙子么站在大太阳底下拉着水管子冲了两把就跑了。”
东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经常到小区来,每回来了冯庆民都要把物业表扬一番:替腿脚不便的老人代缴水费、更换抽水马桶、规划停车位、安装充电桩、清掏化粪池……户内户外,只要列上居民需求清单的,物业都一一满足。
147栋楼3099户几乎全部走访一遍,更换894个楼道灯、清运37车大件垃圾、清理116个楼道小广告,这是刘鹏所带领的物业团队在“试用期”后交上的成绩单。张云对他们的评价是:始于物业,但不止于物业。
虢镇街道老旧小区治理这盘棋在政府引进市场化的物业公司之后被“下”活了。
在街道的主持下,59个老旧小区相继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囊括了区上联建单位、街道、社区和居民等,既支持和配合物业工作,比如召集居民代表大会商议缴纳物业管理费,又对物业公司形成制衡与监督。与此同时,物业党支部也被批准成立。
对于党建引领,刘鹏有自己的见解:党组织可以把多方力量凝聚起来,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互补合作,最终目的是把居民服务好、把小区治理好。刘鹏为这样一个正在重塑的社区“多元共治”网络而振奋,而他尤为看中的,是他享受到的平等与尊重。
总算给老旧小区治理开出了个对症的“药方”,王德武的心病也去了大半。老旧小区有了物业,虢镇街道的居民矛盾纠纷解决“三事分流”机制得以顺利推行。
虽然小事、大事、难事这“三事”看上去并非界限分明,但确实给居民吃下一颗定心丸——“我的事,有人管”。
住在东关小区15年,冯庆民说,他最近体会到了当市民的感觉。

用好小区里的“能行人”
王福清怎么都没想到,自打从陈仓区农业局退休后,他发挥余热的主阵地既不在儿女的小家庭,也不在整天丝竹管弦声不绝于耳的老年活动中心,而是在另一个竞争激烈的“职场”——小区业主委员会。唯一的区别是,干这份工他不领一分钱工资,纯公益。
王福清所居住的佳苑新城小区是虢镇街道西街社区管辖范围内最大的小区,常住人口2000多户。小区居民的来源大致由这几部分构成: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经济条件良好的企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虢镇周边农村和其他乡镇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
从地形图上看,陈仓主城区虢镇街道如同一只龟背,而东西四堡村则与几个城市社区紧紧咬合在一起。在陈仓,城与乡的界限更模糊,更易融合。
“以前讲户籍,如今不存在了。而且现在农村娶媳妇最重要的附加条件,就是男方在城里买套房。”王福清说,归根结底对农民进城买房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实是教育,“农村小学合并,结了婚的没结婚的都在为娃上学做打算。”
如此一来,相比起以家属院为主的老旧小区,佳苑新城这类商品房小区的特点是:基础设施更加完备、环境更加优美,但人员构成更为复杂,业主之间彼此熟悉信任的程度更低,一旦涉及矛盾纠纷更容易给街道和社区的管理造成压力。
在社区工作整整20年,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燕利经历过最大的一场“风波”便发生在佳苑新城小区。
西街社区跟西堡村紧邻,很多单位家属院和商品楼修建时都征得是西堡村的地,佳苑新城小区也不例外。而且当时为了供暖方便,小区的供暖锅炉也建在西堡村。
但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健全与细化,大气污染防治成为各地方政府从严从快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2020年,佳苑新城小区居民接到通知:小区加入全市的集中供热网,每户缴纳入网费2000元,西堡村的燃煤小锅炉按要求即时拆除。
通知一出,如同捅了“马蜂窝”。
居民认为当初买房时这笔费用他们已经交过了,要收入网费找开发商。但供热公司管不了这其中的纠葛,交不上入网费,就没法正常供暖。
“咱家里也有老人孩子,谁能眼睁睁看着大家受冻?”眼看就到供暖季了,刘燕利急得天天住在办公室,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更棘手的是,小区里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私利,开始煽动业主堵路闹事。
担心会有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刘燕利多番联系佳苑新城小区业主委员会,最终的结果却遭遇对方的“不作为”。
关键时刻,有小区居民向刘燕利推荐了王福清。王福清在机关单位上过班,个人素质过硬,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加之为人正直忠厚,又有业主身份,说话容易让人信服。刘燕利当机立断,请来王福清帮忙。
凑巧的是,王福清因工作原因曾经在西堡村驻过村,对这座燃煤小锅炉修建前后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入户劝导居民时,王福清说的既有诚意又有理有据,局面很快得到扭转。
“我给大家伙分析利弊:原先用燃煤小锅炉时供热不稳定,费用也比市政统一供暖的小区高出不少;入了大网以后不仅供热效果好,而且每家每户都给安装流量表,结余下的钱还可以充物业费。如果算经济账,这2000块钱要不了两三年就回来了。”
群众工作做通了,谁来收钱又成了难事。在当时的境况下,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或身份不合适,或不被业主信任。事急从权,由社区“两委”作保,最终所有资金都汇集到王福清名下的银行卡上,统一交给供热公司。
2020年11月15日,佳苑新城小区居民家里的暖气如约而至,刘燕利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从这些事上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业委会的人一定要选好,选不好的话小区里就乱套了。”刘燕利说,尤其大型商业小区,想进业委会的大有人在,但有些人是冲着“权力”来的,想要给自己和亲友谋私利。更有甚者扬言要把小区的物业赶走,自己成立物业公司。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城市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调整,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单靠社区“两委”的力量难以完成。
社区呼唤有能力、有公心、能担当的居民共同参与治理,当好政府、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小区业主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的角色地位越来越重要。
2022年11月29日,佳苑新城小区业委会换届第三次会议在西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
新一届业主委员会的候选人中,有驾校校长、广播电视台职工、退休教师、美容院老板等,王福清也身在其中。为了这次换届,街道和社区做了充分准备,从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公告到历次会议筹备都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候选人的入选条件增添了几条:党员优先、群众推荐,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物业出具无拖欠物业费证明。
“之所以党员优先,是为了给业委会党支部的成立创造条件。”刘燕利补充道,“成立党支部之后,业委会就不再是一个松散的自治组织,而是在社区党总支的领导下有序开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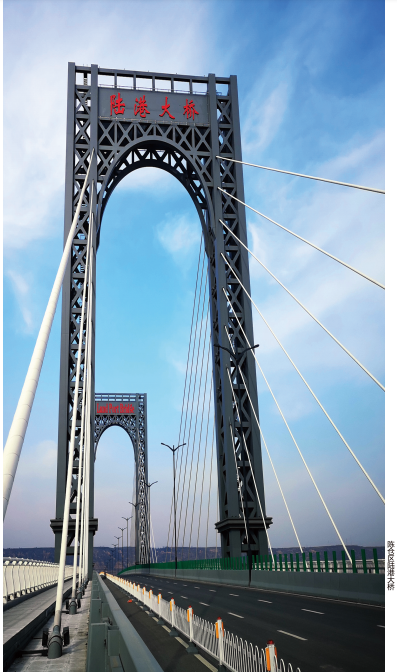
“融入”单位型社区
阳光弥散的午后,陈仓区千渭街道双鸥社区的义工二宝(化名)正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忙活着。
只见他不厌其烦地向过往居民宣传:今天社区在发放“九率一度”测评表,麻烦大伙儿移步去领上一张,表格填好交回之后还可以领取一袋食盐。
他身穿社区志愿者的红马甲,头发再不像从前那样乱糟糟地黏在一起,而是修剪成利落干练的寸头,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退休老党员于宝赠忍不住感慨:“二宝这两年变化实在太大了。”
来社区帮忙,二宝怀着的是一种“报恩”心态。别的不说,多年前他家那间漏雨的房子,是社区干部赶在汛期强降雨到来前请工人修缮的。
二宝家是社区里的困难户。但用于宝赠的话来说,“厂子要是还在,二宝的日子没这么难。我进厂的时候他爸是我师傅,要知道当年我们这个厂一般人是很难进来的,工人们的收入相当可观。”
于宝赠口中的“厂子”,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陕西机床厂。双鸥社区党总支书记王连连手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厂志,里面详细记录了陕西机床厂的不凡出身与光辉成就。
陕西机床厂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兵工厂,1958年为支援地方工农业建设移交给陕西机械局。最鼎盛时期,它是国家机械工业部生产外圆磨床和家电产品的重点大型企业。双鸥社区的名称由来便源于陕西机床厂生产的一款明星产品——双鸥牌洗衣机。
“就像电视剧《人世间》里演的那样,我们这些国营厂的职工习惯了以厂为家,厂子里有医院,有学校,有商店,有澡堂,可以说足不出户就把衣食住行所有的事都解决了。”陕西机床厂原办公室主任冯珠明说,大部分工人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因此并未察觉到正在改变的社会大环境和一步一步逼近的企业生存危机。
2007年,陕西机床厂宣布破产。1000多人下岗,600多人吃低保,曾经灯火通明的厂区道路上,一盏盏路灯熄灭了,萧瑟秋风卷着路两旁法国梧桐上枯黄衰败的树叶,像是在诉说人群中弥漫着的低迷与沮丧。
在厂子破产与父亲去世的双重打击下,二宝的精神疾病愈发严重。尤其他好几次因为房子的事求助无果后,邻居们反映他看人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在陈仓,酒精厂社区、北动社区和双鸥社区等都是典型的单位型社区,辖区居民大部分为本厂职工。陕西机床厂未破产之前,社区治理的任务由厂里成立的专门机构承担。但破产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原机构逐渐无法满足居民对于社会保障服务等多方面的需求。2019年,陈仓区开始派工作人员进驻双鸥社区。
到双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上班的头一天,王连连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栋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楼,两扇木门上挂着一把古老的锁,门口的地板走上去打滑,房间里的暖气片只能当作“装饰”……
但对于王连连来说,工作环境差并不紧要,区委区政府有专项资金支持阵地建设,最难的是他们这些“外人”如何迅速打开局面,赢得居民信任。
双鸥社区的老龄化率高,已经超过40%,王连连便从为老服务入手。她请来陕西省荣复军人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到社区义诊,把医保报销的细则贴在社区宣传栏最醒目的地方。
社区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常年无人修缮,王连连主动对接宝鸡市医保局等包联单位和爱心企业,用“化缘”来的钱给老人们精心布置了练舞房和书画室。
双鸥社区有379名党员,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当年生产线上的工人骨干,党性原则强,关心家国大事。王连连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过道打造成党史学习长廊,定期组织老党员外出参加文化活动,重新唤起他们那份集体荣誉感……
“自从政府接管之后,感觉社区一下子变活了,我们这些退休职工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酷爱走旗袍秀的姚秀萍常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她见证了那些破凳子、烂桌子、裂缝的镜子是如何变魔术般焕然一新,也亲眼看到社区干部面对冲自己拍桌子的居民是如何耐心劝慰。
而她不知道的是,社区里的吸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还有像二宝一样的困难户经常能接到社区干部的电话,嘘寒问暖,询问生活所需。他们的孩子也可能是社区四点半课堂里某个受表彰的少年。
在和居民越来越多的接触中,王连连发现了藏在这里的“秘密”:这些原国营工厂的职工很多是从全国各地迁来的,虽然厂子不在了,但他们中许多人早已把陈仓当成了眷恋的故土,这里有他们青春的记忆、有可依赖的老友和熟悉的家园。
“双鸥社区从单位型社区向板块型社区转型,我们这些人要发挥减压阀和润滑剂的作用。”在王连连看来,社区就像一个港湾,它让居民有苦可以诉、遇难有人帮,“我们一点一滴地做,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它变好。”
来双鸥社区三年半,王连连做了许多事,还有许多想要做。比如她想挖掘厂子里的红色资源搞研学游,而如今由民营企业承包的铆焊加工车间等也可以让学生同时领略现代工业的魅力。
但有一件事她还没顾得上做——社区的几间办公室里至今没有像样的取暖设施。每次姚秀萍来看王连连时提起这事,她总说,辛辛苦苦争取来的钱要先用在民生工程上,“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


